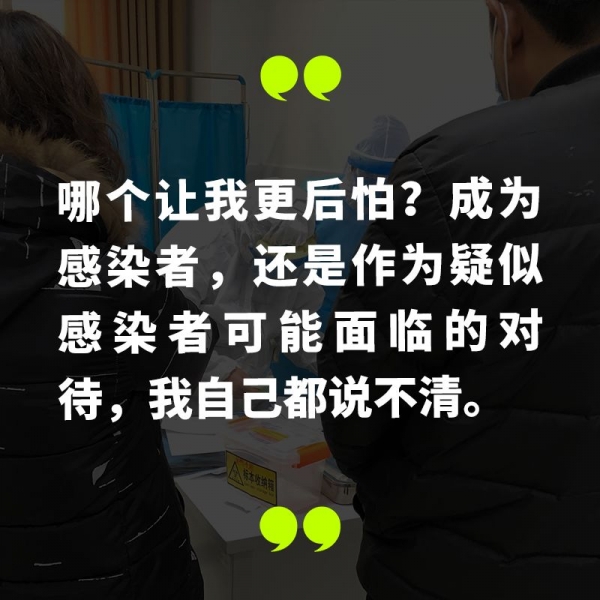武汉酒馆老板:我们停业了,但这座城市没停摆

图源于王粒丁
“跳东湖吗”
我叫光头,2013 年,在武汉开了一家精酿酒馆,从未停止营业过,即使大年三十那一天晚上。

西餐厨师做起中餐也不赖|图片来源 18 号酒馆

广场舞领军者 —— 光头和临时的舞搭子|图源见水印
街上开门的大多是那些往日里生意不佳的店铺。一家老字号热干面店所在的街区被修成过江隧道后,生意差了不少。这家二十年的老店,自开业就没关过门,24 小时营业,现在也还开着。往年酒馆春节营业的时候,一帮人晚上常去吃宵夜。老板娘,我们喊她大姐,就在门口叼着烟,偶尔炸点小吃,自己吃也卖。
王粒丁很好奇它为什么不关门。对方很 “撩撇”(武汉方言,干脆)地说:“我们这家店就没门。” 店里的工人指给王粒丁看,门口就只有一个门框。

硬核的热干面店|图源见水印

在做好卫生的前提下就餐,拒绝人心惶惶|图源见水印
封城后的第一个晴天,我们骑车经过江汉桥,往下望,每隔十米就有个人在晒太阳。东湖边钓鱼的老头,戴着口罩,跟左右的人隔了五米远,特别像网上说的 “北欧式排队法”。过两天再路过的时候,已经一个人都看不见了,气氛越来越紧张。
“要哪样的摇滚”

左边的是光头,他搂着的就是王粒丁|图源自 18 号酒馆

在医院门口等订单的外卖小哥|图源见水印

图源于王粒丁
“跳东湖吗”
我叫光头,2013 年,在武汉开了一家精酿酒馆,从未停止营业过,即使大年三十那一天晚上。

西餐厨师做起中餐也不赖|图片来源 18 号酒馆

广场舞领军者 —— 光头和临时的舞搭子|图源见水印
街上开门的大多是那些往日里生意不佳的店铺。一家老字号热干面店所在的街区被修成过江隧道后,生意差了不少。这家二十年的老店,自开业就没关过门,24 小时营业,现在也还开着。往年酒馆春节营业的时候,一帮人晚上常去吃宵夜。老板娘,我们喊她大姐,就在门口叼着烟,偶尔炸点小吃,自己吃也卖。
王粒丁很好奇它为什么不关门。对方很 “撩撇”(武汉方言,干脆)地说:“我们这家店就没门。” 店里的工人指给王粒丁看,门口就只有一个门框。

硬核的热干面店|图源见水印

在做好卫生的前提下就餐,拒绝人心惶惶|图源见水印
封城后的第一个晴天,我们骑车经过江汉桥,往下望,每隔十米就有个人在晒太阳。东湖边钓鱼的老头,戴着口罩,跟左右的人隔了五米远,特别像网上说的 “北欧式排队法”。过两天再路过的时候,已经一个人都看不见了,气氛越来越紧张。
“要哪样的摇滚”

左边的是光头,他搂着的就是王粒丁|图源自 18 号酒馆

在医院门口等订单的外卖小哥|图源见水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