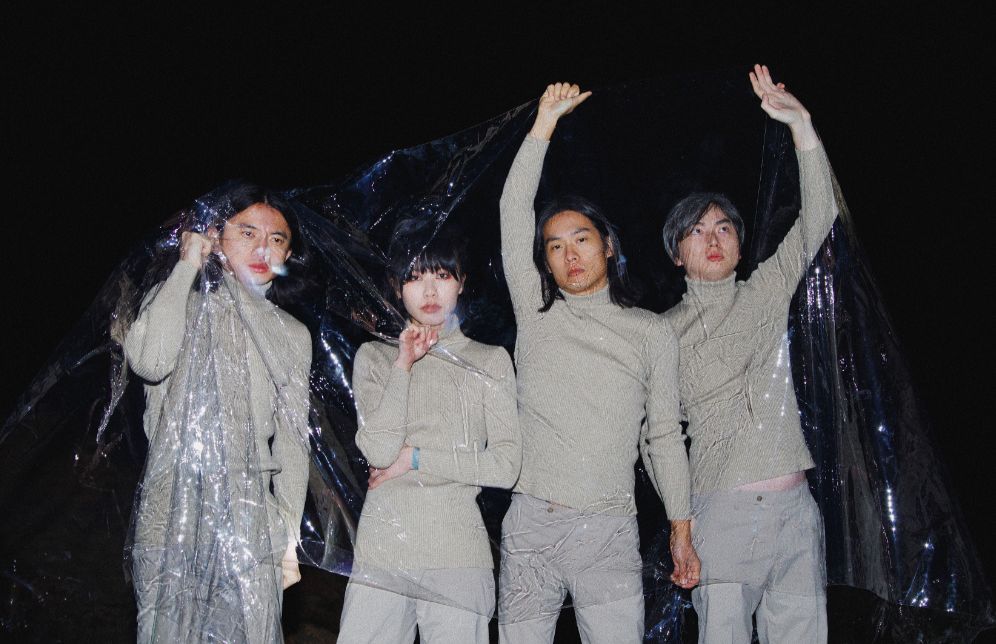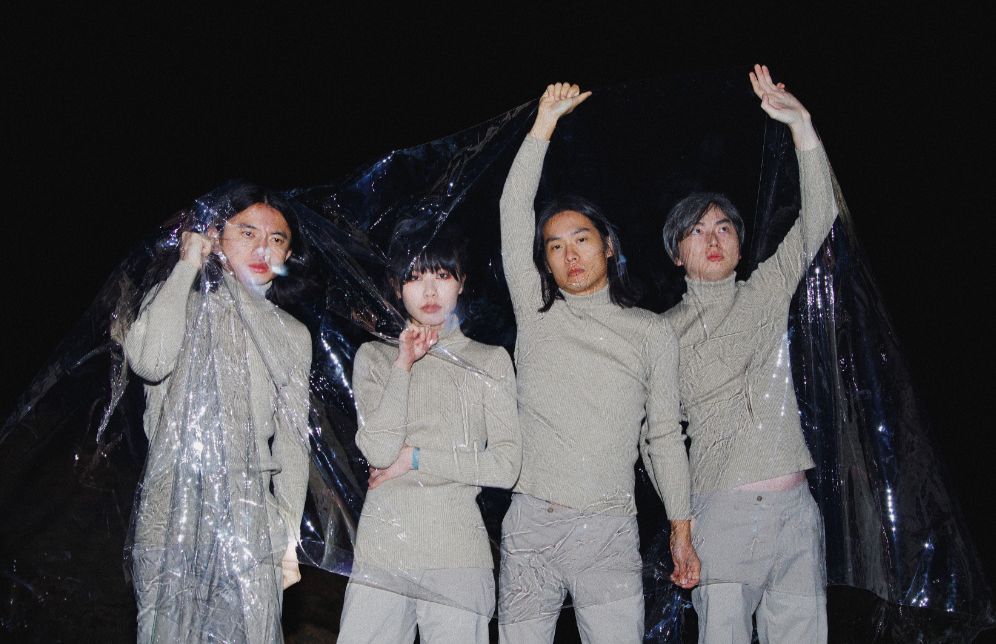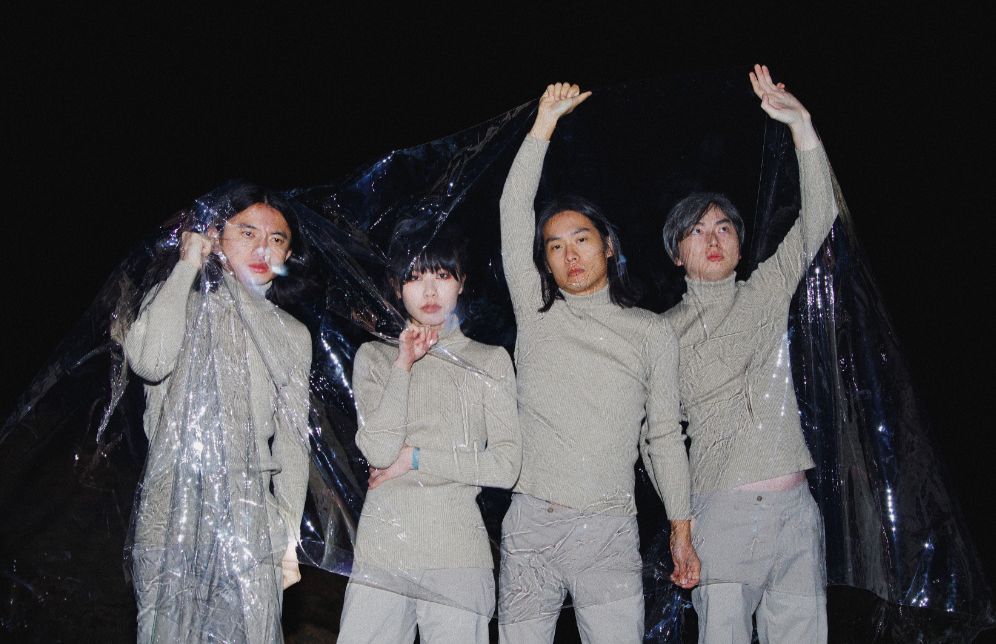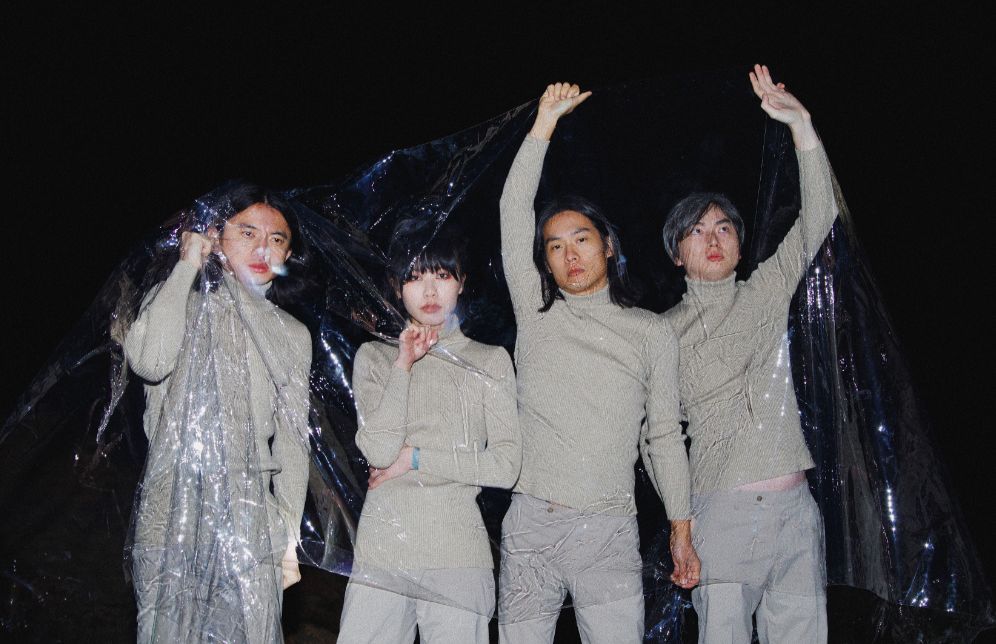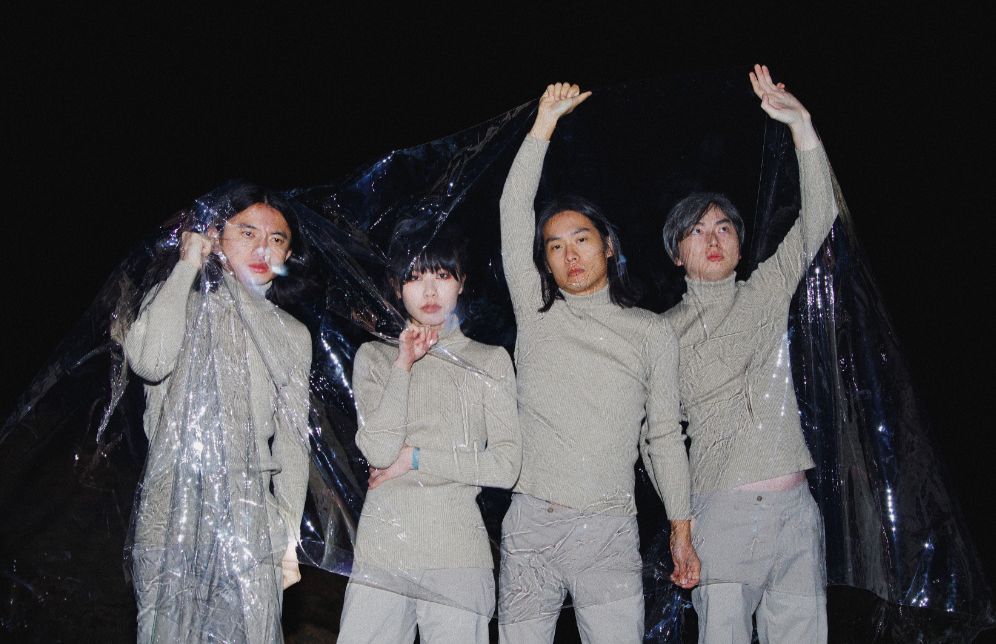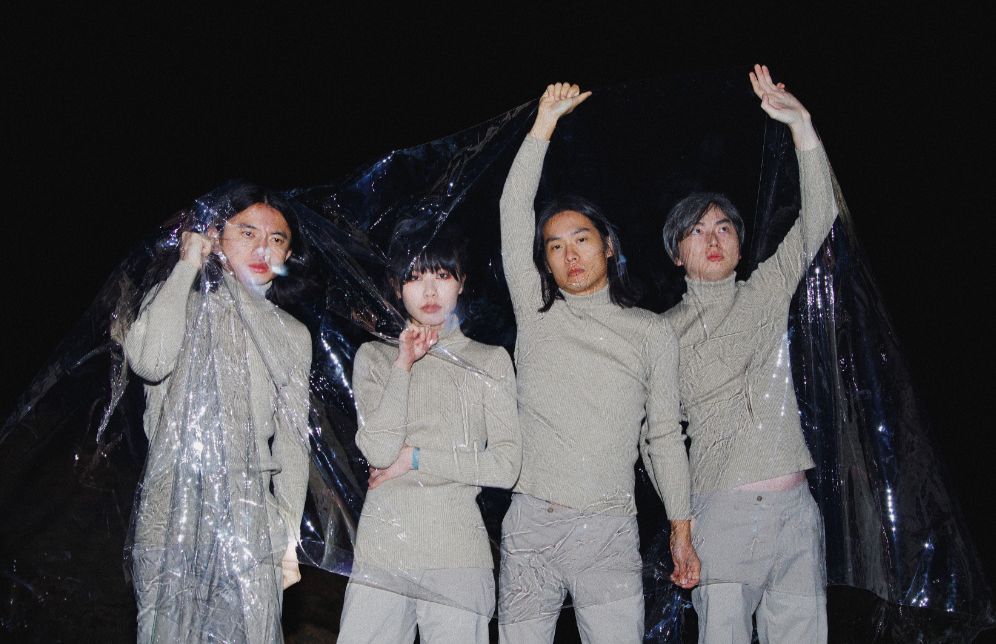别的电波:2013 年我去上海找你的时候你就说想组乐队,但是找不到人?文隽:对,我 2010 年搬到上海,一直想组乐队。因为我不会乐器,必须找乐手,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去玩电子、做DJ,我找不到人,就开始干别的事情 —— 6 年就过去了。有一天晚上杨帆跟刘舸的乐队 TOW 去上海,我去看他们演出,喝多了很兴奋,到处跟人说话。有一个尼泊尔的朋友德斯道,在武汉上学,跟陆炎、左翼他们混,我就狂跟他说我在上海6年了没有找到人一起玩乐队,我说汤庭会弹吉他,但是我们就没有鼓手,然后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贝斯手。文隽:反正那天晚上我认识了张云,我也喝多了,说我们来排练,张云就很开心地答应了。汤庭:我开始做绝对纯洁之前看过两个印象比较深的演出,一个是杨帆组的新乐队来上海,另外一个就是工工工,这两个乐队对我刺激挺大的。去看现场特别让人兴奋,给我本身带来刺激。文隽:我有一天从迪卡侬开车出去,是一个地下车库,开出去的时候视野很窄,只看到对面高楼上竖着写的四个大字:“绝对纯洁”。红色的,非常严肃的字体。我觉得很魔幻,很荒唐,非常庄严的四个大字竖在那,你仔细一想这四个字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它很残酷,因为它太庄严,又无法达到,特别像一个玩笑。反正我被震撼了,就记住了这么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