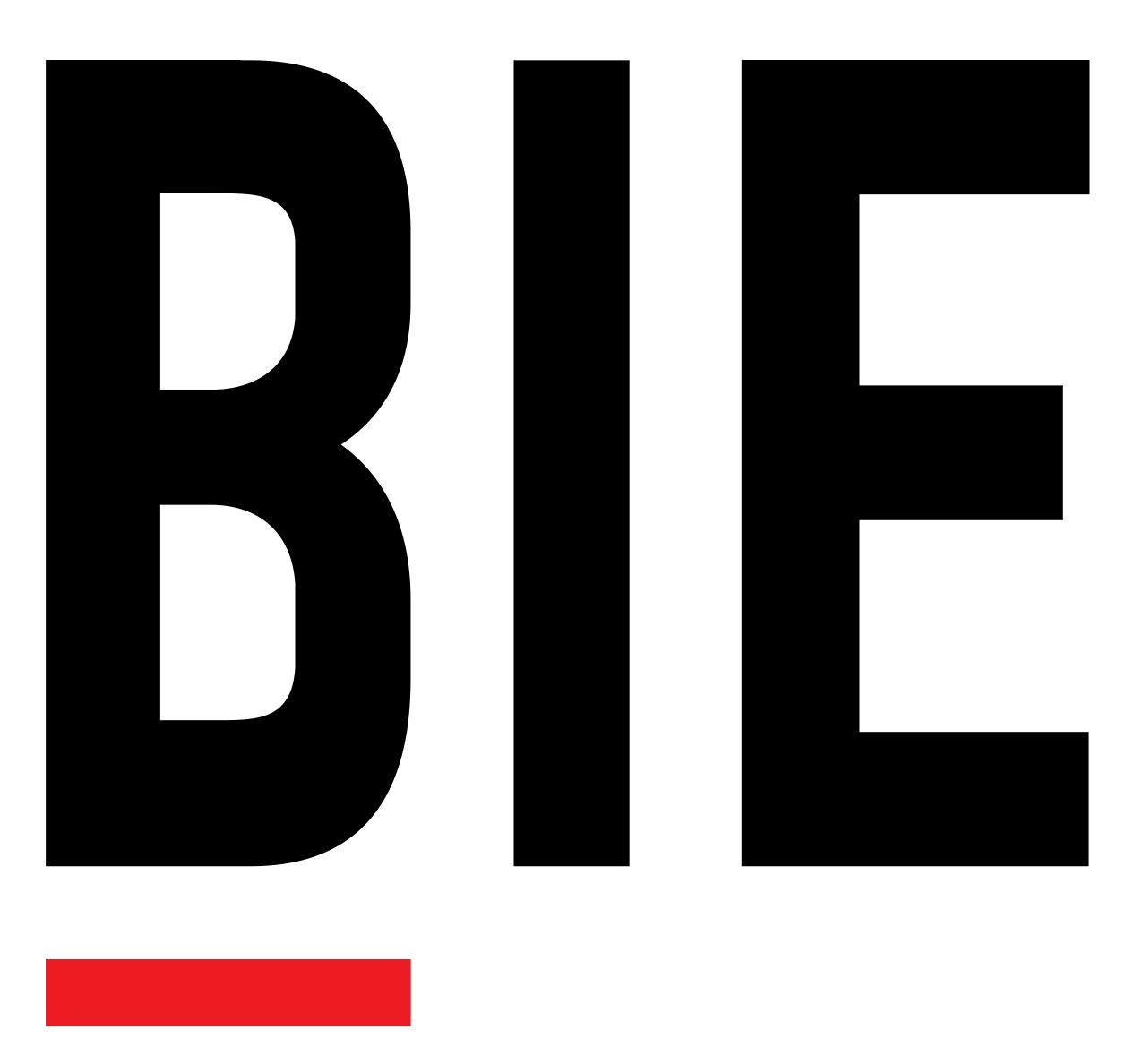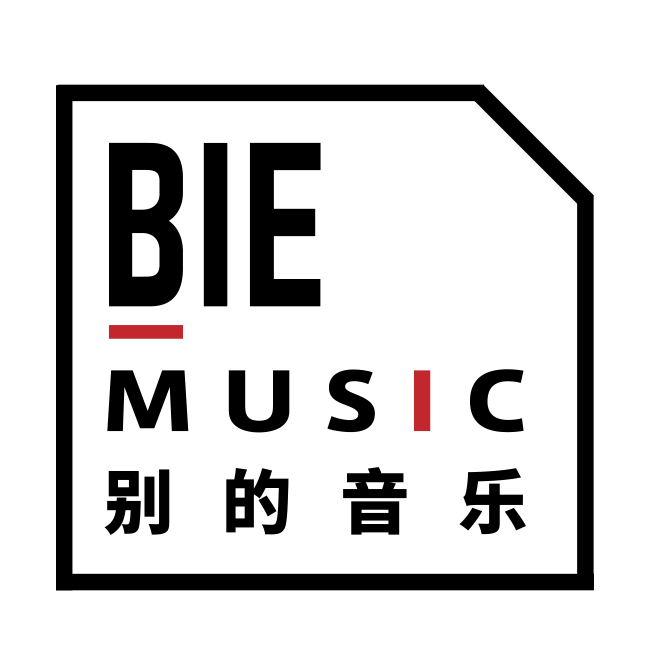作为国内的指标俱乐部之一,上海ALL Club的公开求援引起了许多场景内外的关注。令人振奋的是,这次求援并没止于空泛的口号,而正演变为国内俱乐部场景最为隆重的“庆祝”活动。自4月30日公布消息和五月份完整演出时间表以来,以SVBKVLT、Asian Dope Boys和OIL为代表的众多国内知名电子音乐厂牌、派对主办及同行场地方几乎让重拍响彻上海的每个夜晚;随着下半月的到来,SHCR上海社区电台、Elevator俱乐部及Genome Mbp 6.66厂牌等派对组织者也即将相继登场; 在全球俱乐部场景正遭受重创的绝望时刻,ALL和身边每个参与者展现出作为共同体的坚韧、团结,以及本地场景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ALL CLUB五月活动时间表
在所有5月份的活动中,除了用音乐积极表达对多元价值观念的赞许,ALL还选择呈现由音乐向外延展出的不同生活方式及艺术项目。其中,与Shelter(ALL的前身)和ALL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策展人李佳桓策划了一场影像展览——“流连”。该展览由对末世景象的想象引出, 作品来自9组或与ALL结缘很深或从未去过ALL的艺术家和团体,作品主题触及艺术乃至人性在动荡末日中的存续方式等问题。
我们为李佳桓对club文化的深入思考着迷,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对他进行了简短采访。稍有意外的是,他在回复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因精神家园面临危机而有的急迫或哀叹;相反地,他关于末世概念与现实重合的情形有着富有启发性的思辨——“听说ALL的经济困难这个消息时,反而是整个疫情期间少有的感觉有‘希望’的一天,因为短期目标一下子明确了:我们要想办法守住我们的庇护所。”当我们向他转述一些对于俱乐部举办艺术展览存有质疑的声音时,他用平静、克制的回答展现出过人智慧。这次的对话让我们建立了某种信心。也许在终将到来的末日里,“俱乐部之死”的命题会成真,但俱乐部人的精神肯定不会消散。

《入迷》,陈天灼,2019年,影像截图
*今晚(5月14日)9点,展览将特别放映艺术家陈天灼的作品《入迷》。该片为陈天灼12小时行为艺术作品的3小时精简纪录版。
在你开始阅读以下的问答前,请允许我们代表李佳桓和ALL Club向你发出诚挚地邀请。“流连”是一场接受任意金额门票捐赠的免费活动,其所得全部收入都将被捐赠给ALL作为度过难关的资金。同时,我们还希望你能关注,支持以上活动时间表中的其他活动,积极投身到丰富多彩的俱乐部生活中。如果你不在上海,也请一定留意自己身边的各种独立音乐社群。它们的存续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值得我们每个人贡献出一份力量。

受访者:李佳桓(Alvin Li)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平时在做些什么,又是怎样和ALL以及国内的club场景联系到一起的。
我是个写作者和策展人,工作中主要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平时写艺术评论、策展,偶尔也会写虚构、情色短篇小说和自小说(autofiction)。我2010年寒假从美国回国第一次去Shelter,后来14年搬回国后老是在外面玩,慢慢地就和围绕Shelter的一帮音乐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16年开始策划一些影像放映活动,开始和Shelter合作,后来Shelter关门ALL现身后这种合作也一直保持。我在上海最好的几位朋友,比如Eli Osheyack,也都是SVBKVLT的音乐人。
地下club音乐场景的爱好者和参与者对反乌托邦和后末世(dystopia、post-apocalypse)的概念都不陌生;而我们的现实现在似乎正滑向这种境地;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形,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1月底一直到4月因为疫情在全国、全球的蔓延我一直都挺颓的,和很多朋友交流的一个共鸣是,原来apocalypse虽然有我们所幻想的暴力和死亡,但没想到整个过程并不是短促而充满震慑力的,而是这么漫长、折磨,甚至无聊、沉闷的。那段时间每天唯一督促我至少起床面对现实的来源是和全球各地的很多朋友通过各种媒介平台保持交流,一起思考在接下来的后新冠时代的生态、经济废墟和紧闭的国家边界下怎么继续实践,捍卫共同体。其实听说ALL的经济困难这个消息时,反而是整个疫情期间少有的感觉有“希望”的一天,因为短期目标一下子明确了:我们要想办法守住我们的庇护所。这个情形让我想到了人类学家Anna Tsing的书”Mushroom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中文译本好像台湾出了,叫《末日松茸》)中谈到的后资本废墟中生存和协作的可能性。我在这种围绕着ALL产生的协作共生中体会到很强烈的存在感。

《消失的邀请》,Julian Charrière,2018年,影像截图
这次ALL向公众发出的呼救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论。俱乐部文化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少分歧。你觉得小众群体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特性真得要走向和大众隔绝甚至对立的方向么?你又怎么看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关系?
我常年朋友圈关闭,对于这次的争论只有所耳闻,也一直忙着准备展览没时间去关注/参与,没法在此给出洞见。
作为临时展览活动的策划者,针对有些舞客批评的“俱乐部应该只为跳舞服务,不应该充斥着各种实验展览”,你怎么看?
首先,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批评,这种纯粹主义还挺宝贵的,手动点赞!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且动机迥异,但这让我想到90年代以林其蔚为首的很多台湾实验声音制作人曾经聊到的一种现象,即视觉主导的当代艺术空间(美术馆等等)当时对声音实践萌发的兴趣,想要去做它们;这帮激进的声音实践者提出,这是一种主流文化资本对声音的收编,并将讨论拓展到其他现象谈体制对反抗力量的收编。我想,这次,在一个以音乐、跳舞为主的空间来做一影像展览,是不是可以一种视为反客为主,对主流体制的收编和利用呢?(笑)
说回正经的:面对ALL的经济危机,这场展览的初衷非常纯粹,就是想通过把我的工作领域(当代艺术系统)里的一些的朋友邀来ALL,看看展(其实ALL的空间非常适合做影像和雕塑类展览),也让ALL的朋友们接触下好的当代(视觉)艺术,促成一些“跨界”——虽然剥去当下体制形成的距离,声音、视觉于我而言都是艺术,只是媒介不同而已。所以如果舞客们对这番好心仍抱有怀疑,我也只能抱憾了。
其次,俱乐部只能跳舞这种纯粹主义也许正是一些空间无法生存的原因。我认为一个空间的揉杂性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在一个俱乐部这样一种熔炉般的环境中。纵观俱乐部的历史它从来就是一个声音、行为等不同媒介的实践发声、发生的场域。如果上海会真开个只能跳舞的俱乐部,酷,我想也我也会去支持它的生存。
互联网背景下,线下场地对你和朋友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一直是非常依靠身体的在场的;在这次新冠之前我长期被周围的朋友批评我是一个很差的朋友,因为我社交媒体很少用,平时只要不在一个城市了,别人发短信我也基本很少回,还因此毁了好几段友情。经历这次新冠后我的虚拟存在有大大提升,有在花些精力去维持远距离的联系。
你是否有具体想象过“俱乐部之死”——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你又能怎么办?
如果物理的在场和身体接触这两个俱乐部的必要条件因为病毒这样的不可控因素被剥夺了,只要还是有一群人去齐心协力想办法,那么就有可能依靠技术让它变形成其他替代性的存在形式。接下来它还是不是club就只是一个修辞问题了。前几个月通过Zoom平台发生的云上派对其实也有一些了,比如在美国的Bubble T…等等,这只是些初步的尝试,但也揭示着一个开端和方向。比如在柏林,似乎大部分俱乐部9月之前都无法开张,它们和那边的DJ/艺术家们依靠政府的补贴在生存着。那么,他们会生产出怎样的替代手段也是挺值得保持关注的。
其实很多俱乐部,虽然空间仍在,它却早已经死掉了,甚至从来没有活过,因为它无法,也无意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共同体。
可以用一句话试着概括下ALL对你的意义么?
ALL是我的家,生活在上海的一大理由。
//采访、编辑:Ivan H.
WE CAME TO LINGER 流连
策展人语
“流连”是一份礼物,一场致敬,一封情书。这是一场对ALL 近来财务危机的紧急回应,而这次危机很有可能导致ALL 在五月底被迫关闭⸺距离现在仅剩两周而已。我们无法接受要失去它的可能,尤其是处在这样一个边界高墙树立、地缘纷扰动荡、糟心病毒激化乱局的关头,我们更迫切需要关切、捍卫本地的共同体和实践。
“流连”萌发于和德文单词Clubsterben(译作“俱乐部之死”)的偶然邂逅。近来,随着新冠病毒以叫人窒息的节奏席卷全球,这个词语也开始在网上疯传,描述一个在全球范围的夜场迫在眉睫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问题:一个俱乐部的死亡,解散,消失......意味着什么?眼看一个熟悉的场景瞬间变得陌生,就像是在一场演唱会的末尾,encore 之后,作为歌迷仍在台前流连、撕心裂肺地吼叫的我们,突然意识到偶像不会再回来;一瞬间,灯光猛烈照射下、依然被汗水浸湿的舞台,即刻溶解,继而凝固成一堆沉闷、冰冷的钝物。你的心跳错过了一拍,紧接着问自己: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以“俱乐部之死”这个极有可能发生的末日景象为出发点,我们的展览会在这个特别的五月中的两个晚上,把ALL 改造成一个展览空间,呈现来自世界各地九位艺术家和团体的影像作品以及一组摄影作品。面对俱乐部可能将至的早夭,这场向它致敬的展览中的作品共体现了三大主题:表达敬意,或流露仰慕之情;探究社会仪式在塑造身份认同和归属想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这一过程在俱乐部和其他共同体空间中绝非鲜见;草拟万物迁移至在线空间、甚或人性也将飘摇迷失的未来世界可能的蓝图。参展艺术家有的是ALL 家族的一员,有的则从未到过这里。然而出于对那些所曾逗留过的场所的记忆(那涉及到身体的律动、触及诱惑、肾上腺素,并关乎亲密),于此他们都慷慨地同意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我还是鼓励大家付出全部的时间投入展览。去流连、辗转、沉浸于作品间。如果你想放声大笑请随意,即使笑中带泪也没有关系。假如这个月真的是ALL 最后的时光,这将会是一段我们短暂为伴的美好回忆。但如果我们能挺过难关,我相信之后我们会永远永远羁绊更深,牵连更紧密。
- 李佳桓

展览时间
5月13日 周三 - 5月14日 周四
19:30pm 至 深夜
入场费 自由捐赠
ALL CLUB
上海 襄阳北路17号楼(近长乐路)
作为国内的指标俱乐部之一,上海ALL Club的公开求援引起了许多场景内外的关注。令人振奋的是,这次求援并没止于空泛的口号,而正演变为国内俱乐部场景最为隆重的“庆祝”活动。自4月30日公布消息和五月份完整演出时间表以来,以SVBKVLT、Asian Dope Boys和OIL为代表的众多国内知名电子音乐厂牌、派对主办及同行场地方几乎让重拍响彻上海的每个夜晚;随着下半月的到来,SHCR上海社区电台、Elevator俱乐部及Genome Mbp 6.66厂牌等派对组织者也即将相继登场; 在全球俱乐部场景正遭受重创的绝望时刻,ALL和身边每个参与者展现出作为共同体的坚韧、团结,以及本地场景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ALL CLUB五月活动时间表
在所有5月份的活动中,除了用音乐积极表达对多元价值观念的赞许,ALL还选择呈现由音乐向外延展出的不同生活方式及艺术项目。其中,与Shelter(ALL的前身)和ALL有着紧密合作关系的策展人李佳桓策划了一场影像展览——“流连”。该展览由对末世景象的想象引出, 作品来自9组或与ALL结缘很深或从未去过ALL的艺术家和团体,作品主题触及艺术乃至人性在动荡末日中的存续方式等问题。
我们为李佳桓对club文化的深入思考着迷,在展览开幕的当天对他进行了简短采访。稍有意外的是,他在回复中没有流露出任何因精神家园面临危机而有的急迫或哀叹;相反地,他关于末世概念与现实重合的情形有着富有启发性的思辨——“听说ALL的经济困难这个消息时,反而是整个疫情期间少有的感觉有‘希望’的一天,因为短期目标一下子明确了:我们要想办法守住我们的庇护所。”当我们向他转述一些对于俱乐部举办艺术展览存有质疑的声音时,他用平静、克制的回答展现出过人智慧。这次的对话让我们建立了某种信心。也许在终将到来的末日里,“俱乐部之死”的命题会成真,但俱乐部人的精神肯定不会消散。

《入迷》,陈天灼,2019年,影像截图
*今晚(5月14日)9点,展览将特别放映艺术家陈天灼的作品《入迷》。该片为陈天灼12小时行为艺术作品的3小时精简纪录版。
在你开始阅读以下的问答前,请允许我们代表李佳桓和ALL Club向你发出诚挚地邀请。“流连”是一场接受任意金额门票捐赠的免费活动,其所得全部收入都将被捐赠给ALL作为度过难关的资金。同时,我们还希望你能关注,支持以上活动时间表中的其他活动,积极投身到丰富多彩的俱乐部生活中。如果你不在上海,也请一定留意自己身边的各种独立音乐社群。它们的存续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多样性值得我们每个人贡献出一份力量。

受访者:李佳桓(Alvin Li)
请你介绍一下自己是谁,平时在做些什么,又是怎样和ALL以及国内的club场景联系到一起的。
我是个写作者和策展人,工作中主要活跃在当代艺术领域,平时写艺术评论、策展,偶尔也会写虚构、情色短篇小说和自小说(autofiction)。我2010年寒假从美国回国第一次去Shelter,后来14年搬回国后老是在外面玩,慢慢地就和围绕Shelter的一帮音乐人变成了很好的朋友。16年开始策划一些影像放映活动,开始和Shelter合作,后来Shelter关门ALL现身后这种合作也一直保持。我在上海最好的几位朋友,比如Eli Osheyack,也都是SVBKVLT的音乐人。
地下club音乐场景的爱好者和参与者对反乌托邦和后末世(dystopia、post-apocalypse)的概念都不陌生;而我们的现实现在似乎正滑向这种境地;你怎么看现在的情形,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1月底一直到4月因为疫情在全国、全球的蔓延我一直都挺颓的,和很多朋友交流的一个共鸣是,原来apocalypse虽然有我们所幻想的暴力和死亡,但没想到整个过程并不是短促而充满震慑力的,而是这么漫长、折磨,甚至无聊、沉闷的。那段时间每天唯一督促我至少起床面对现实的来源是和全球各地的很多朋友通过各种媒介平台保持交流,一起思考在接下来的后新冠时代的生态、经济废墟和紧闭的国家边界下怎么继续实践,捍卫共同体。其实听说ALL的经济困难这个消息时,反而是整个疫情期间少有的感觉有“希望”的一天,因为短期目标一下子明确了:我们要想办法守住我们的庇护所。这个情形让我想到了人类学家Anna Tsing的书”Mushrooms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中文译本好像台湾出了,叫《末日松茸》)中谈到的后资本废墟中生存和协作的可能性。我在这种围绕着ALL产生的协作共生中体会到很强烈的存在感。

《消失的邀请》,Julian Charrière,2018年,影像截图
这次ALL向公众发出的呼救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论。俱乐部文化仍处于边缘地位的情况下,其内部不同的族群也有不少分歧。你觉得小众群体为了保全自己的独特性真得要走向和大众隔绝甚至对立的方向么?你又怎么看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关系?
我常年朋友圈关闭,对于这次的争论只有所耳闻,也一直忙着准备展览没时间去关注/参与,没法在此给出洞见。
作为临时展览活动的策划者,针对有些舞客批评的“俱乐部应该只为跳舞服务,不应该充斥着各种实验展览”,你怎么看?
首先,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种批评,这种纯粹主义还挺宝贵的,手动点赞!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且动机迥异,但这让我想到90年代以林其蔚为首的很多台湾实验声音制作人曾经聊到的一种现象,即视觉主导的当代艺术空间(美术馆等等)当时对声音实践萌发的兴趣,想要去做它们;这帮激进的声音实践者提出,这是一种主流文化资本对声音的收编,并将讨论拓展到其他现象谈体制对反抗力量的收编。我想,这次,在一个以音乐、跳舞为主的空间来做一影像展览,是不是可以一种视为反客为主,对主流体制的收编和利用呢?(笑)
说回正经的:面对ALL的经济危机,这场展览的初衷非常纯粹,就是想通过把我的工作领域(当代艺术系统)里的一些的朋友邀来ALL,看看展(其实ALL的空间非常适合做影像和雕塑类展览),也让ALL的朋友们接触下好的当代(视觉)艺术,促成一些“跨界”——虽然剥去当下体制形成的距离,声音、视觉于我而言都是艺术,只是媒介不同而已。所以如果舞客们对这番好心仍抱有怀疑,我也只能抱憾了。
其次,俱乐部只能跳舞这种纯粹主义也许正是一些空间无法生存的原因。我认为一个空间的揉杂性是很有意义的;尤其是在一个俱乐部这样一种熔炉般的环境中。纵观俱乐部的历史它从来就是一个声音、行为等不同媒介的实践发声、发生的场域。如果上海会真开个只能跳舞的俱乐部,酷,我想也我也会去支持它的生存。
互联网背景下,线下场地对你和朋友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一直是非常依靠身体的在场的;在这次新冠之前我长期被周围的朋友批评我是一个很差的朋友,因为我社交媒体很少用,平时只要不在一个城市了,别人发短信我也基本很少回,还因此毁了好几段友情。经历这次新冠后我的虚拟存在有大大提升,有在花些精力去维持远距离的联系。
你是否有具体想象过“俱乐部之死”——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你又能怎么办?
如果物理的在场和身体接触这两个俱乐部的必要条件因为病毒这样的不可控因素被剥夺了,只要还是有一群人去齐心协力想办法,那么就有可能依靠技术让它变形成其他替代性的存在形式。接下来它还是不是club就只是一个修辞问题了。前几个月通过Zoom平台发生的云上派对其实也有一些了,比如在美国的Bubble T…等等,这只是些初步的尝试,但也揭示着一个开端和方向。比如在柏林,似乎大部分俱乐部9月之前都无法开张,它们和那边的DJ/艺术家们依靠政府的补贴在生存着。那么,他们会生产出怎样的替代手段也是挺值得保持关注的。
其实很多俱乐部,虽然空间仍在,它却早已经死掉了,甚至从来没有活过,因为它无法,也无意形成自己的文化和共同体。
可以用一句话试着概括下ALL对你的意义么?
ALL是我的家,生活在上海的一大理由。
//采访、编辑:Ivan H.
WE CAME TO LINGER 流连
策展人语
“流连”是一份礼物,一场致敬,一封情书。这是一场对ALL 近来财务危机的紧急回应,而这次危机很有可能导致ALL 在五月底被迫关闭⸺距离现在仅剩两周而已。我们无法接受要失去它的可能,尤其是处在这样一个边界高墙树立、地缘纷扰动荡、糟心病毒激化乱局的关头,我们更迫切需要关切、捍卫本地的共同体和实践。
“流连”萌发于和德文单词Clubsterben(译作“俱乐部之死”)的偶然邂逅。近来,随着新冠病毒以叫人窒息的节奏席卷全球,这个词语也开始在网上疯传,描述一个在全球范围的夜场迫在眉睫的危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问题:一个俱乐部的死亡,解散,消失......意味着什么?眼看一个熟悉的场景瞬间变得陌生,就像是在一场演唱会的末尾,encore 之后,作为歌迷仍在台前流连、撕心裂肺地吼叫的我们,突然意识到偶像不会再回来;一瞬间,灯光猛烈照射下、依然被汗水浸湿的舞台,即刻溶解,继而凝固成一堆沉闷、冰冷的钝物。你的心跳错过了一拍,紧接着问自己: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以“俱乐部之死”这个极有可能发生的末日景象为出发点,我们的展览会在这个特别的五月中的两个晚上,把ALL 改造成一个展览空间,呈现来自世界各地九位艺术家和团体的影像作品以及一组摄影作品。面对俱乐部可能将至的早夭,这场向它致敬的展览中的作品共体现了三大主题:表达敬意,或流露仰慕之情;探究社会仪式在塑造身份认同和归属想象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而这一过程在俱乐部和其他共同体空间中绝非鲜见;草拟万物迁移至在线空间、甚或人性也将飘摇迷失的未来世界可能的蓝图。参展艺术家有的是ALL 家族的一员,有的则从未到过这里。然而出于对那些所曾逗留过的场所的记忆(那涉及到身体的律动、触及诱惑、肾上腺素,并关乎亲密),于此他们都慷慨地同意成为展览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我还是鼓励大家付出全部的时间投入展览。去流连、辗转、沉浸于作品间。如果你想放声大笑请随意,即使笑中带泪也没有关系。假如这个月真的是ALL 最后的时光,这将会是一段我们短暂为伴的美好回忆。但如果我们能挺过难关,我相信之后我们会永远永远羁绊更深,牵连更紧密。
- 李佳桓

展览时间
5月13日 周三 - 5月14日 周四
19:30pm 至 深夜
入场费 自由捐赠
ALL CLUB
上海 襄阳北路17号楼(近长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