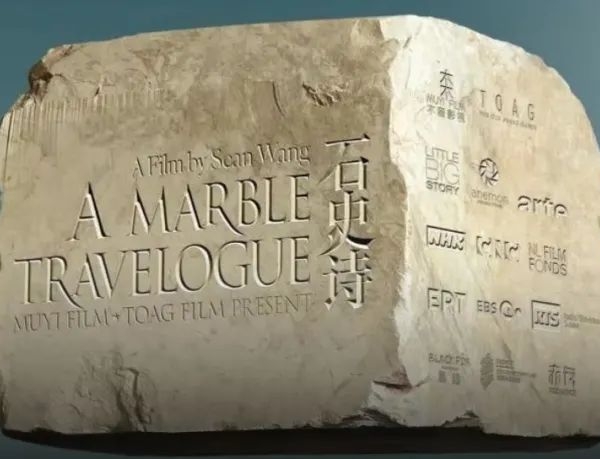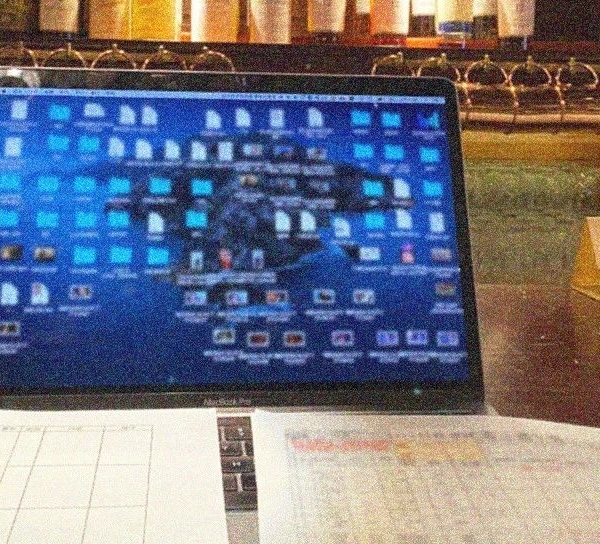0

旷野中有歌,有神,有鬼,还有持摄像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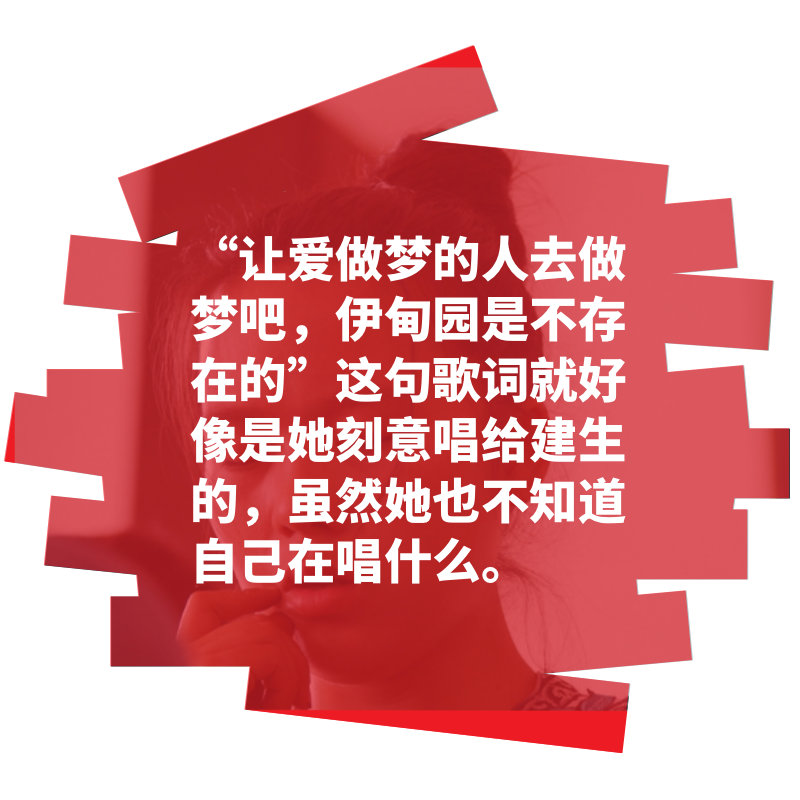






旷野中神和鬼
.png)
“我们苗族人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是神啊,请指引我们通向未来的道路。”——《旷野歌声》
一直以来,小水井村的苗族村民们笃信村子里有鬼,却不知有神。在《旷野歌声》另一版的电影海报上,那条挂在树上的裙子就据说是被鬼挂上去的。
陈东楠导演告诉我,村子里自一直流传着关于鬼的传说,有时是偷裙子的鬼,有时是附在人身上的鬼,生病了是鬼搞得鬼,盖房子时砸伤了手也是因为鬼。直到现在村子里还保留着苗族传统中的巫医看病方式:生病了以后拿个煮熟的鸡蛋在身上滚一滚,滚完后掰开,根据蛋黄的纹路,判断这 “病鬼” 是怎么缠上你的。





亚萍和建生
.png)
“他们在纽约时演出唱了《让我们的花园繁茂生长》(Make Our Garden Grow )这首歌,刚好建生的妻子唱的是 'Let dreamers dream what worlds they please / Those edens can't bt found' (让做梦者去做梦吧,伊甸园是不存在的) ,这句歌词就好像是她刻意唱给建生的,虽然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唱的是什么。” —— 陈东楠


“红歌歌手”亚萍


因为在婚姻的这条道路上真的很不容易,放下自己很难,牺牲自己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当你坚持下来,不论是什么样的生活领导你,你都不要去结束这个生命。虽然我们生活在旷野当中,但是神还是会为我们开大路,所以选择牺牲生命这样的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做了。



闯入旷野的汉族女人
.png)
“那天演出完了以后,建生他就来找我,一副要打架的架势,握紧了他的拳头,浑身颤抖,大声说:‘你才是王八蛋’!” —— 陈东楠



小水井合唱团的团员们

山雾缭绕的小水井村

写在最后:旷野中持摄像机的人
.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