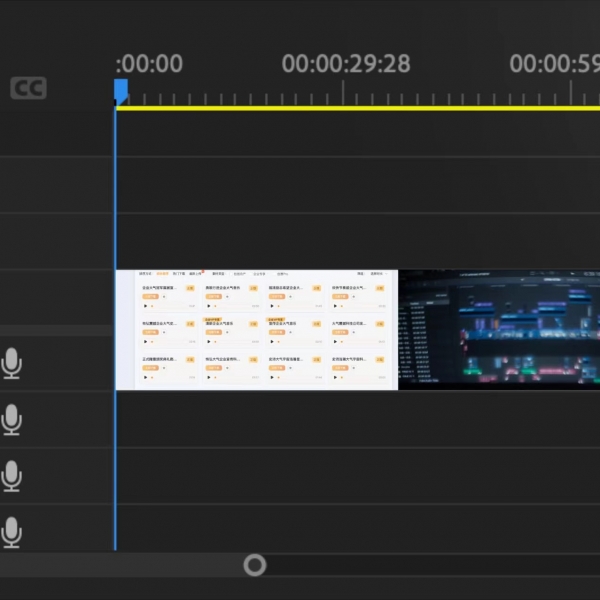三年找工作的经历证明了,名校毕业的我果然是个废人
由于本人很早就学了一个约等于 “屠龙之技” 的艺术专业,尚未成年就开始产生寻找自身价值的紧迫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你甚至现在还能查到我那时提的沙雕问题:

人生大事,在线求助挺急的
焦灼的疑问伴随我多年,直到一个 “fight club” 时刻偶然降临。某一天,在音乐会开始前的喧响之间,我盯着前排的红丝绒椅背,忽然意识到人生很可能是个循环式的陷阱:拿生命换取报酬,再将所得的钱投入消费,犹如活在一个巨型培养皿,周而复始。当然你不能说这全是徒劳:吃的饭变成屎浇铸庄稼,然后才又有饭吃。这是社会生生不息的秘密。但这个消极论据不能说服年轻的我,为了让自己投入工作,我得找到更积极的动力。
于是第二天我坐在图书馆里拿起纸笔开始进行一番严密的论证。如果工作是为了理想,那菲薄的工资就无异于对理想的羞辱;如果工作是为了赚钱,那我在玄妙的音乐理论中所投入数年就将成为一个笑话;如果工作是为了让自己体面光彩,那么我要么得找到一份好赚钱的工作,要么得找到一份能实现理想的工作。完了,这根本就是一个逻辑的死结。但聪慧的我在这个死结中发现了一个突破口,我意识到工作也许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让你在追求以上词汇之前,先找点事情干,避免从社会的运转中漏出去。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究竟能去干什么呢?
这时我终于领悟:其实我真没什么学以致用的手艺。像我这样缺少 hard skill 的废柴学生,等待我的将是就业市场上一堆含义不明的 “通用型” 职位(比如,新媒体小编)—— 这是留情面的说法,说白了就是 “谁都能干,不行换人”。

图源网络
所幸我年近半百的一半时明白这个道理还不算晚!当晚我就打开了 “北大青鸟” 官网首页。他们不仅贴心地按照性别(虽然分类不细)推荐适用的专业,还详细剖析了每种工作的就业前景和学习成本。这都不重要,关键是我爱上了他们的 slogan:“够酷、够炫、多赚钱”。短短七个字,直击待业青年心窝。精准营销啊这是,等的就是我这茬韭菜。
但我比他们预料得还着急。彼时的互联网创业者飞在天上人人仰望,消费的泡沫还饱满而绵密。关掉网页我就给刚成立的时尚电商发去了 CV,得以在翘课之余给人瞎 JB 写点 FASHION 文章,以便把一些别人的钱引到另一些别人的手里。从人设经营、数据分析到共享办公体验个遍以后,被榨得像甘蔗渣似的我意识到自己写的东西就好比在虚拟世界放了个屁 —— 说好听点就是我又虚无了。
于是我决定:下一份实习得是高雅的、经典的,手握玫瑰让他人闻闻香那种的。我去了一家古典艺术经纪公司,成了写字楼下端着星巴克的白领狗。早晚打卡,午休时去 SPA 上瑜伽课,还紧急从众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而我的工作,说来惭愧,就是在一个不通风的格子间给艺术家制作 PPT。老板没出现过,我们像勤劳的工蜂履行每个早已定型的流水线步骤。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绝无可能挺过这种生活。

站在写字楼下心情沮丧,不禁赋诗一首
这跟我想象得可差太远了!
毕业在即,大家都在找工作,我又开始跟着瞎 JB 投简历。可选的地方就那么几个,有了前续经验,这些招聘骗局在我眼前纷纷抖落画皮,我一眼就能看透那些冠冕堂皇的岗位本质:流水线上搬砖的、卖弄口舌的、听人使唤的、忍气吞声的。几个月后,最后一个叫嚷着 “找不到工作啊!” 的倒霉孩子都尘埃落定了,而我全部都被拒了 —— 这就好比相亲时你嫌弃的对象没看上你,除了自尊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损失外,心里松了一口气。最后,我被辅导员推荐去学校某个行政部门干活,以免当年就业率被我拖了后腿。
至于干的是什么活,很惭愧,除了打杂、跑腿、给老师们瞎 JB 添乱以外,什么也没干。但收获还是有的,那就是以管窥豹地体会到 “体制” 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妙就妙在你永远说不出它哪里错,但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身在其外的时候觉得它是罪魁祸首,身居其内又觉得一切都无比合理。
小时候我一度智力有些问题,听不懂老师讲话。我听见了每一个字,但组合起来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二十年以后,我又在 “领导的谈话艺术” 里找到了童年的感觉:他似乎在关心我,又似乎在批评我,我仿佛有些地方令他不满意,但他又不告诉我错在哪。谜一样的男人,捉摸不透。

图源网络
好玩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说我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每天守在一台传真机面前,给里面吐出来的每一张纸盖章,比如 “关于开展校园爱国活动”、“关于网络舆情情况工作通知”、“关于 xxxxxxx 动员工作”,等等,不一而足。数周以后你会看到全体师生整齐划一地在做同一件事而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而做,做给谁看,只有我知道 —— 操纵他们的是从虚空里吐出的某一张神秘的纸。
我的工作内容之二是在某个偏僻阴暗的小隔间汇总同学们的荣誉成绩,再一一写成新闻广而告之。时间久了心理难免失衡,就好比给人做嫁衣做到眼瞎的老处女,揽镜自照心茫然。也不知从哪一天起,我的脑海里忽然反复响起赵辛楣对方鸿渐说的话。那晚,他们在甲板上推心置腹地闲聊,方鸿渐问他,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赵辛楣很诚恳地对他说:“你是个好人,但全然没有用处。”
第一次读这话时,我还在上小学四年级。假如那时的我看到自己现在这副样子,一定心情复杂:“你看那个人,她好像一条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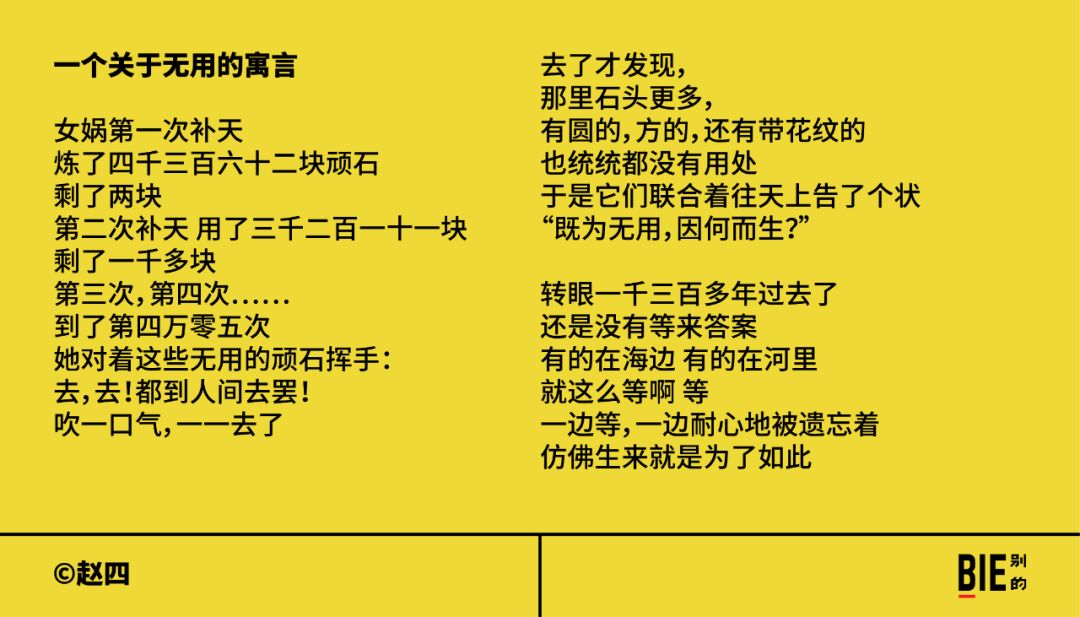
好人青年心情沮丧,再次赋诗一首
说到这里,本人眼高手低、定位不清、耽于幻想、志大才疏的负面形象相信已经部分坐实了。不用怕,不会有人比那时的我更看不起我自己。我既没有挣大钱,也没有找到一个体面的 title 然后像拧螺丝钉一样把自己舒舒服服地拧进去。这几年的试错充分证明,我这也不会干,那也不会做,更要命的是,我在哪里都呆得不自在,在哪里都格格不入。简而言之,我废了。
说来不怕大家笑话,最绝望的时候我甚至求助于玄学。我认真研究了自己的八字,上网搜索自己适合什么职业。得出的结论令我大跌眼镜:道士。这还没完,我甚至还去查了佛学院招生简章,结果发现我已经超龄了。现在想想,我之所以绕那么一大圈其实无非是想逃避那个既定的命运:考上艺术学院以后当一个艺术老师,再去教学生如何考上艺术学院。
我想寻找自己的道路。
经过了一个 “每天醒来都有一个朋友在暴富” 的时代,没有过幻觉那是不可能的。但我总觉得,上了那么多年学,大家出来以后干的事情都差不多,或者干脆继续没完没了地念书,总归是有点问题。在前所未有的丰盛年代,青年人的想象力不应匮乏至此。
总而言之,我找工作的这段经历大概可以归结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费尽心思地想融入主流语境,当一枚有用的螺丝钉,却发现无处可去。她不喜欢那些工作,工作更不喜欢她。更糟糕的是,在毕业生严重过剩的今天,她都没有资格说 “我不想干”。
“当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正面是一个鼓励,反面就成了一个威胁让你不寒而栗,要是对社会没用,你的个人价值将面临极大危机。我相信与我一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很多,他们正在困兽犹斗于无边无际的自我质疑。
最后以一个小故事作为结束吧!
若干年后有小朋友问我:老阿姨,你二十多岁时候在哪里?在干嘛?
我答道:“那时候我刚从纯净水加工厂里被排放出来,却发现到了大海里,到处都是水,早就水满为患了,我只好去饮料厂、香水厂、牛奶厂,却发现自己格格不入。周围人眼看形势不妙,只好两眼一闭挣扎着回炉,指望出来当个高级水。但也不是谁都能高级起来,比如四阿姨,后来就去了泔水加工厂,再后来去了废物利用厂,再往后就该去火葬厂啦。”
小朋友又问:那既然用不到这么多纯净水,为什么还要生产呢?
我回答:你不懂,工厂只负责生产,大海才是筛选器。没有我们这些“泔水”,怎么衬托那些高级水呢?
小朋友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那我将来也要去纯净水厂,当一个高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