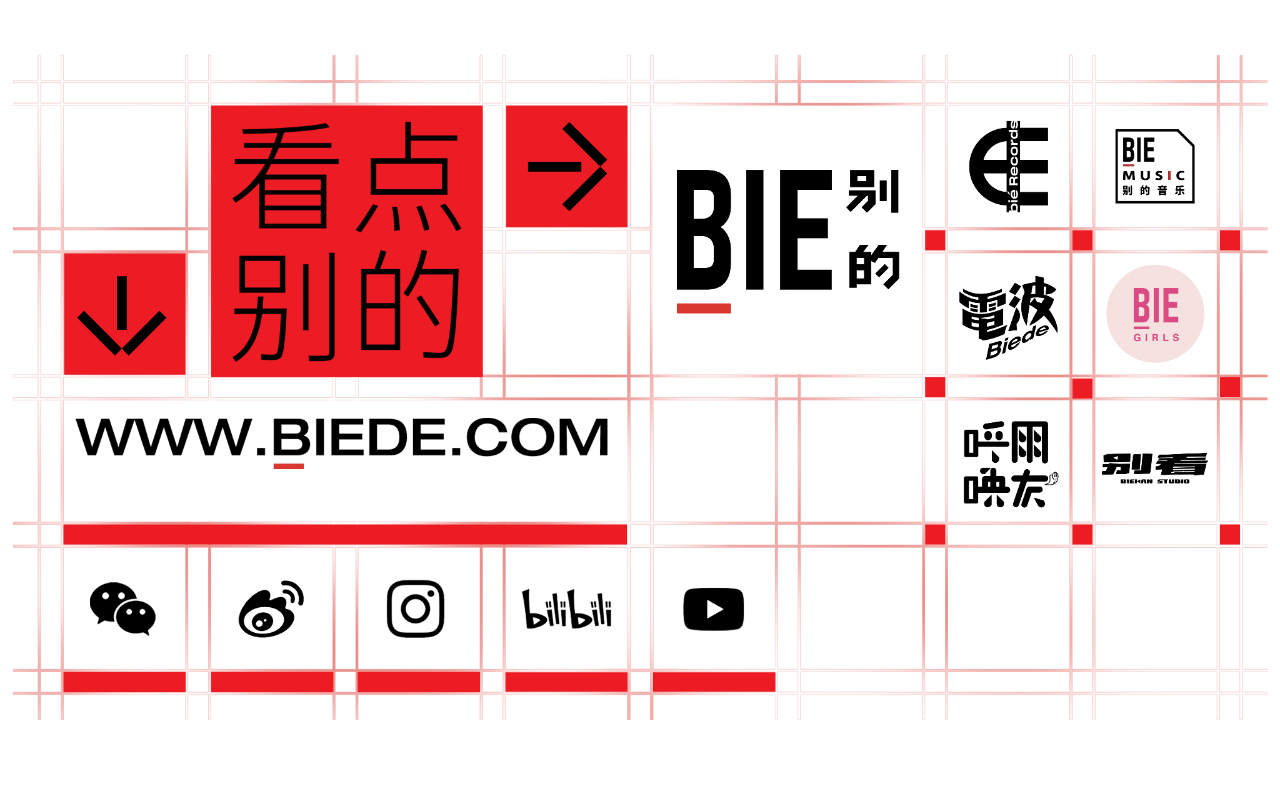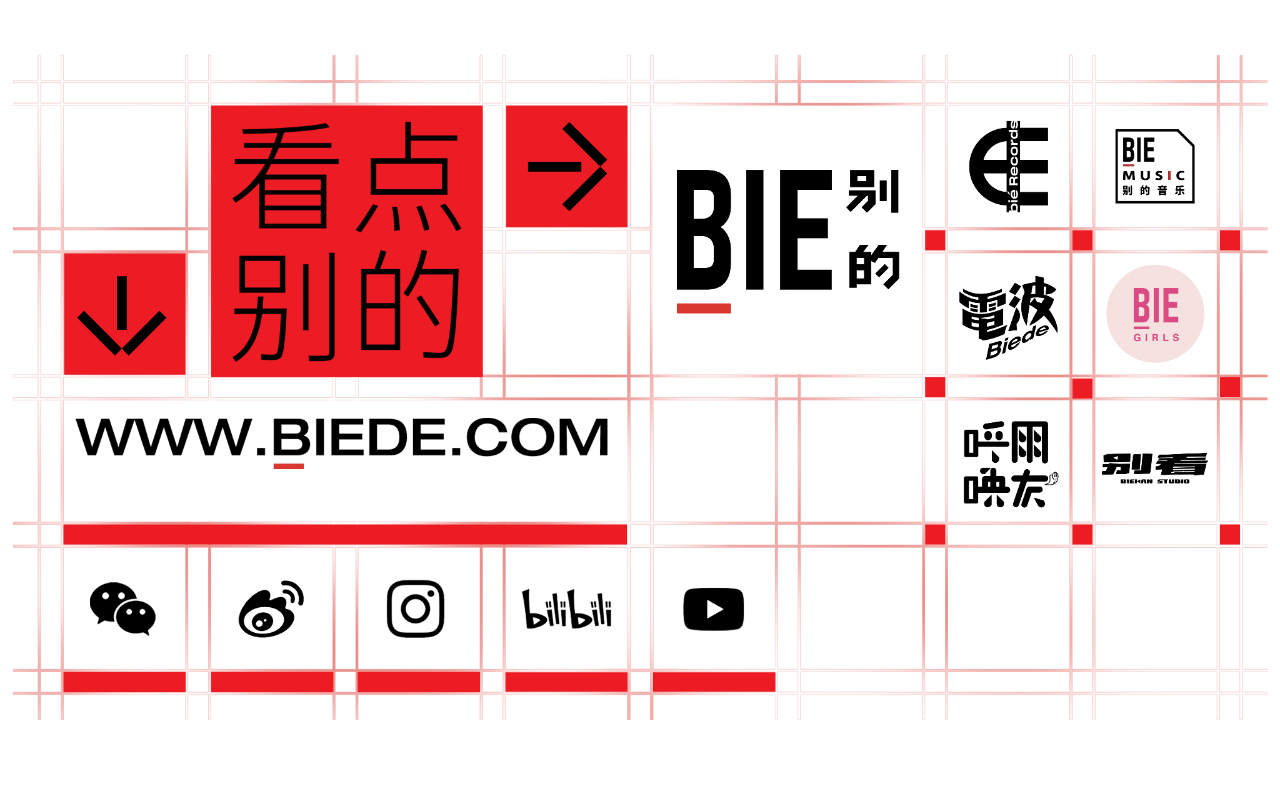在春节这样阖家团圆的日子里,有一类人的心理阴影会被无限倍放大。ta 们可能存在着家庭关系破裂、事业生活不够 “体面”、和父母有冲突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但 ta 们的心理咨询师在这段时间也要放假,很难给予及时的帮助。向朋友倾诉就更不合适了,哪个朋友愿意在大年初一就被扫兴呢?甚至于,ta 们不仅要小心翼翼地藏好悲伤的秘密,还不得不在收到新年祝福时,打起精神回应。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在众人狂欢的除夕夜,我们确认了彼此就是正在 emo 着的同类。互相发了十几个哭哭的表情之后,我们决定,与其一起哭,不如一起写一篇文章。尽量冷静地审视和描述痛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写完后,我们对自己的接纳好像多了一些。毕竟,我们终于不用再假装 “新年快乐”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