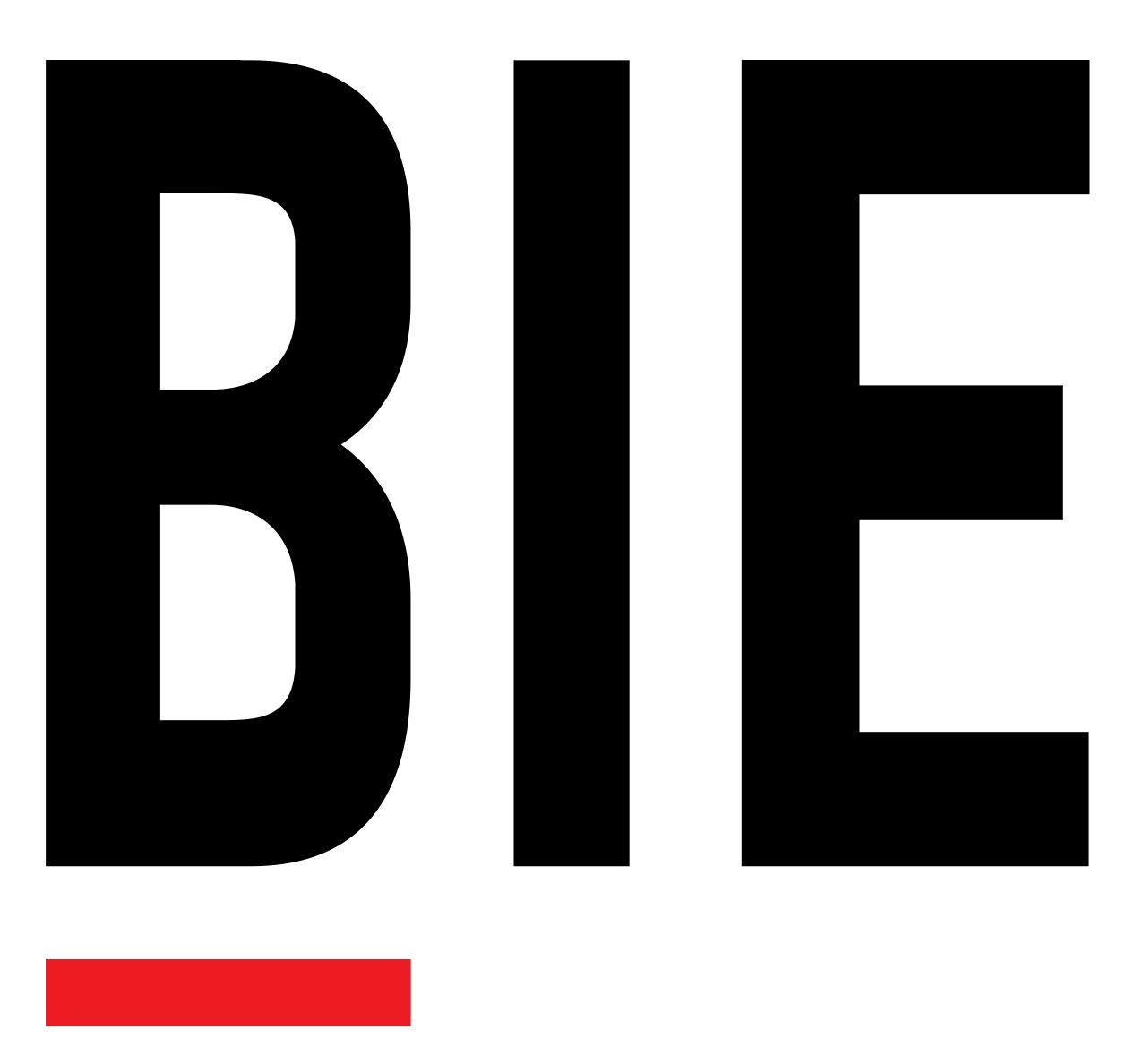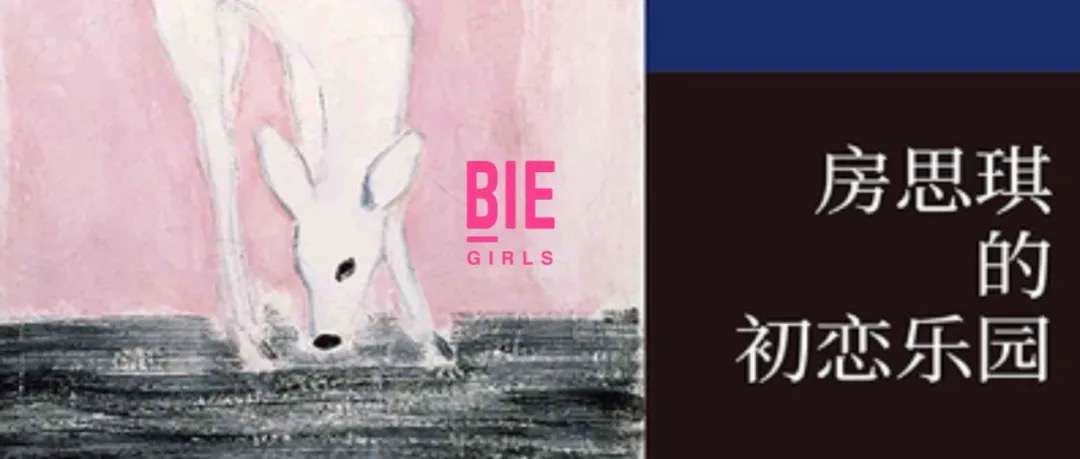
走出“房思琪”式陷阱:警惕男人打才华牌
安 妮
▼
前段时间,由于 “女权男骗炮事件” 接连暴雷,“有才华的男性” 一时成了豆瓣热点话题。从 “你愿不愿意嫁给赌博嫖娼负债累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到 “有才华的男的是不是更容易骗到小姑娘”,一时吸引到不少讨论度。许多女性网友纷纷以亲身经历证明,有些男性确实会利用自己在文学、艺术、哲学领域的经验来获取性资源。在最初关于这一话题的豆瓣动态里,发帖人@谭香山这样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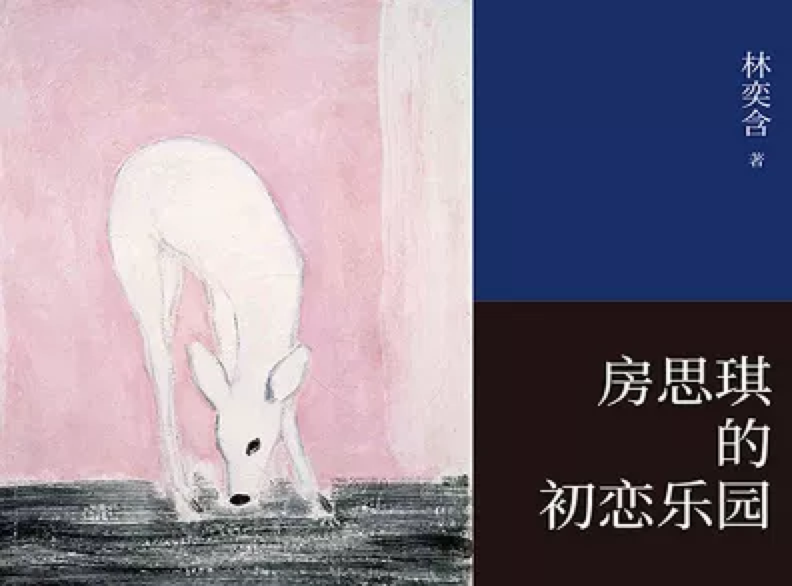
在房思琪的故事里,老师李国华的诱骗手段无外乎:肯定她的才华,并巨量展示自己比她更高的才华。
这样的观点也引发了许多质疑。总结下来,无非两种类型:
一种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一些网友会把这直接归结为 “女性问题”,认为原文发言是女性 “感情用事” 、缺乏 “世俗智慧乃至生活常识” 的体现。有趣的是,具有这种想法的除了男性也包括不少女性。
另一种则是指出这种利用才华或经验骗炮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此类观点的持有者基本上都是男性,他们认为,这种事情本质上是权力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运用 “男性” 和 “女性” 这样的说法有加剧二元性别对立的危险。“才华” 能够成为资源只是因为它能够被转换为话语权,“骗炮” 的表象之下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接下来我想对这两种回应再作一番质疑:
第一种质疑者显然是无视了群体普遍性与个体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女性容易感情用事” 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再典型不过的性别本质主义话语。我们当然无法否认,男性与女性在诸多方面的确存在差异,但有些差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父权社会制度规训的结果。而那些 “我没有这种体验,我也不能理解你的体验,所以这种体验没有道理” 的逻辑,则是无比傲慢的。
当我们在说 “女性往往如何如何” 时,当然不是在说所有女性都是如此。要知道,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不会比同阶层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更小。“女性往往如何如何” 所表达的只是,女性相对同阶层的男性更容易遇到某些情况。我们不可能脱离阶层地去单纯讨论性别。
第二种质疑者更是直接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性别中的权力关系本身就是不平等的。的确如他们所说,骗炮本质上是权力问题,但性别问题也是权力问题的一部分。在性剥削加害者里,男性比例远远高于女性,更不用说二元性别体系之外的 LGBTQ+ 群体,ta 们所处的位置太过边缘,以至于发出的声音都难以被听见,而对于挤压 ta 们生存空间有着最大责任的同样也是占据话语权最多的男性群体。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立” 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这种对立并不是男性与女性两个人群之间的对立,而是父权主导的权力中心与所有非主流人群之间的对立。
除此之外,对于这一现象的原因,谭香山本人提到的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世界没有先例,而所有的声音都在说我们不行,在大部分文学故事中,给我们的角色都是一个文学家的妻子、情人、秘书、凝视的对象、想象的实现。” 这并不是否认女性文艺工作者的存在,但比起男性,她们的数量实在太少太少。女性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只能扮演妻子、情人的角色,在文艺作品之外,女性更是被视作猎物、潜在的性对象。
事实上,大部分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领域都是如此。关于针对音乐领域性别关系的研究指出,女性总是被欢迎成为消费者和被消费者,唯独不是生产者。这样一来,男性不仅在创造性产业中占据主导权,他们还不自觉地为产业构建了 “合适” 的女性形象。即使看似主动参与的女性实际上也在被男性所定义,不可避免地陷入男性凝视的漩涡,成为欲望投射的客体。英国学者安吉拉·莫克罗比将父权结构生产体系下的女性工作者描述为 “一种廉价劳动力资源”,在这里,成功不取决于她们的才华,而更多关于外貌、人际关系等其他因素。
而当一个女性,一旦与她所身处场景中的男性有了这样的联系,就很难在凝视中拥有独立人格。正如朱迪·巴特勒在著名的《性别麻烦》一书中所说,性别角色使女性所面对的场景、共同体归属更加复杂,因为 “性别化” 只针对于女性,男性从来不会因为性别被特殊看待,他们从来都是这个体系中 “普遍的人”。
这样的局面显然就是父权制之下性别权力关系不平等所造成的。而当这种文化场景中的不平等牵扯到了性与婚恋,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在传统性别教育里所灌输的父权制主导的伴侣关系中,仿佛就应该是男性更强势、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男性通过展示力量来增强性吸引力,女性则通过示弱达到同样目的。这样一来,参与到文学艺术哲学神话中的男性也更容易成为被崇拜的对象,进而加以利用为自己谋取性资源。而相比于才华男在婚爱性市场畅通无阻,“女博士” 却长久以来被污名化。女性有才华、有能力,非但不能成为一个加分项,反而会被当作婚恋市场中的弱点而受到嘲笑。
对于习惯占据权力高地的一些男性来说,要他们对自身所拥有的特权进行反思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早已渗透入我们生活的各种场景,成为这个巨大秩序机器的一部分,大部分人都早已习惯这就是 “正确的观念”,连为其合理性合法性辩护都没有必要。
而那些容易被这样的男性吸引的女孩,一方面由于受到父权制下两性观的影响、对善于利用自己经验和 “才华” 的男性产生滤镜,另一方面也因为从小接受打压式社会教育,很容易产生自卑心态。尤其当对文学艺术等男性主导的领域产生热情时,这种自卑也极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对 “成熟引领者” 的隐秘渴望。正如谭香山所说,女性似乎只有通过一个 “男性中间人” 才能进入文学,但其实 “我们只是喜欢文学但没有信心而已”。
所幸看到这一点就还不晚。我们想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才华男骗炮” 绝对不是一个花边新闻式的八点档话题,而是一个严肃的、危及人格的致命毒瘤。它的变体可以是性骚扰女学生的教授,可以是性侵粉丝的乐手,更可以是让房思琪痛苦问出 “文学是不是巧言令色” 的李国华们。只要它的底层逻辑建构依然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以此作诱饵的施暴者。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到它,反思它,继而摧毁它。